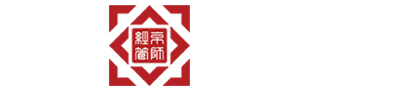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数字经济,属于二十大报告所说的“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对于全面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一、数字经济对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作用
哈佛大学教授波特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优势时的基本单位。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波特进一步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在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等四个方面,要能将这些要素交错运用,形成企业自我强化的优势,才是国外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或摧毁的国家竞争优势。当下,数字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 GPTs) 的广泛应用,聚合产生了数字经济新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大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数字消费带来的需求条件变化、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带来的产业重构、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新战略,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来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数字人口”优势,数字产品应用场景广泛,这些给数字企业“双创”提供了肥沃土壤,众多“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使得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起来。2012—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从11万亿元增加到45. 5万亿元,年均增速为15. 9% ,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在全球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叠加影响下,在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我国数字经济2021年依然保持 16. 2% 的高增长,业已成为并将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二、以国家战略统筹数字经济发展
波特认为“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它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国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制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延续市场与技术发展的核心。中国政府敏锐地抓住了当前百年变局的“机会窗口”,坚持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行动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第五篇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分别对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进行了战略规划。为落实数字经济战略规划,2021 年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有效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八个方面确立了重点任务。为加强数字经济战略规划的统筹协调和落实机制,我国2022年建立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为牵头单位、20个部门组成的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国家各个部委大都制定了行业数字化转型规划和措施,各省份围绕数字经济及其具体业态纷纷出台了促进条例、战略规划及产业政策。这种部业间竞争和地区间竞争的态势,将会形成“以竞争促增长”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
在消费互联网基础上的数字产业化方面,民营企业成为“领头羊”。随着数字经济下半场即产业互联网的兴起,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成为所有企业的不二选择,作为国民经济主导的国有企业必将扮演“主力军”角色。对此国务院国资委2020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工作的通知》,系统明确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方向、重点和举措,中央企业据此都已制定了数字化转型规划的具体方案,转型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可以预见,随着“国民共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和国家竞争新优势将愈发凸显并得以持续。
三、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发展数字经济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需要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扬长”的同时,坚持把 “补短”作为重中之重。
一是突出加强数字技术的原始创新。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形成世界创新高地。创新包括原始创新和应用创新,我国应用创新比较迅猛,原始创新相对滞后。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源头,我国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操作系统等底层数字技术创新虽然取得重要进展,但由于国际风云突变,一些核心技术被“卡脖子”,一些关键产业链被冲击,一些重要人才被限制。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一刻也不能停下,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创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面向国家重大科技需求进行“有组织科研”,聚焦基础研究,致力于原始创新。还应意识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等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不是技术本身难以研发,而是密密麻麻的“专利墙”和标准兼容、互联互通互操作等问题在作祟。在这种情况下,可通过“有组织科研”模式致力于关键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也可“另起炉灶”实施国产化替代战略以绕过各种“专利墙”,还可另辟蹊径研发颠覆性技术实行“变道超车”。无论何种路径,都需充分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以实现二十大报告所讲的“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二是加快实现技术标准国际化。技术创新既需动力机制也需压力机制,技术既要创新出来,也要有效扩散出去,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化成为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所必需的两大制度支持。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同时制定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 年) 》和《国家标准 化发展纲要》。知识产权保护旨在激励、保护科技创新而被法律赋有的专有权,具有排他性; 技术标准是具有公共资源属性的通用技术要求,具有公共性。数字技术专利数量已居世界专利总量的首位,但专利滥用现象较为严重,甚至盛行“专利流氓”( patent troll) ,这就阻碍了技术扩散。技术标准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通过标准必要专利的FRAND( 公平、合理、无歧视) 原则承诺,总体上有助于技术扩散,但也时常以其独占和排外机制引起行业技术标准的固话老化,导致“技术锁定” 现象。这种情况下,以保护创新作为宗旨之一的《反垄断法》就有必要介入,制止知识产权和标准领域形形色色的垄断行为。因此,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促进技术扩散中寻求动态平衡以推动持续技术进步,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议题。2019 年开始,中国在《专利合作条约》( PCT) 框架下申请专利的数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对技术标准化重视不足。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上,应统筹协调知识产权战略、标准化战略、反垄断战略,实现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自主可控,同时不断增大技术标准制定的国际话语权。
三是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先行,需要建设高速泛在、 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网络连接设施、新型感知基础设施、新型算力设施、前沿信息基础设施等。( 1) 在建设泛在智能的网络连接设施方面,我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光纤网络接入带宽实现从十兆到千兆的指数级增长,移动网络实现了从“3G 突破、4G 同步、5G 引领”的跨越。2021 年底,我国已累计开通 4G 基站近600万个、5G 基站196. 8万个,全国所有地级市和县城城区实现5G全覆盖,实现全国“村村通宽带”。在致力于5G商用不断普及的同时,我国正在超前布局 6G 网络技术储备,网络基础设施业已全面支持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为下一代互联网平滑演进升级做好了准备。( 2) 在建设物联数通的新型感知基础设施上,通过感知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融合应用,可实现了人机物的全面感知和泛在连接。目前我国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达16. 7亿,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量突破1600亿。随着工业互联、智慧农业、智能车联等领域的发展,物联网应用将会持续扩张。今后需要继续贯通“云、 网、端”,围绕智能感知、新型短距离通信、高精度定位等关键共性技术进行重点突破。( 3) 在构建云网融合的新型算力设施上,我国近五年来算力年均增速超过 30% ,2021 年底,全国在用超大型、 大型数据中心超过450个,智算中心超过20个,算力规模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今后要实施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工程,加强国家超级计算设施体系统筹布局。 ( 4) 在建设前沿信息基础设施上,我国正在推进以卫星通信、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前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空天地海立体化网络和应用示范工程。在全国几十万亿元的“新基建”中,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将占多数,这将进一步筑牢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是把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数字经济发轫于消费互联网,但工业互联网注定成为数字经济“新蓝海”。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工信部已经发布《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制定工业大数据标准,促进数据互联互通,将工业互联网从企业层面扩展到地区和区域层面,为构建全国工业互联网奠定基础。2021年底,我国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已覆盖 45 个国民经济大类,工业APP数量突破60万个,建成了700多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较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家,连接工业设备超过7800 万台( 套) 。按照我国《“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到2025年建成120个以 上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成5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70%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实现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需要指出的是,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提升效率,更深层次的作用在于通过其“产消合一”( prosumption) 机制,助力企业实现从大规模生产走向定制化生产,有助于宏观上缓解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
(原载于《经济研究》2022年11期,作者戚聿东,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KR18PNrgpbMhZiXReOg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