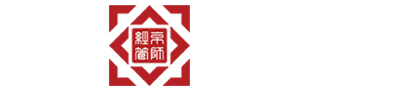(原载于《董事会》2025年第3期,作者高明华,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
在规范的公司治理中,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负有战略决策和对经理层的监督之职权。然而,在国企公司治理实践中,董事会形似而神不至的情况却普遍存在,这源于国企复杂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职权过度交叉和界区模糊,使得看似清晰的董事会职权清单,在实践中却难以落地。因此,破解国企董事会职权清单之惑,首先需要了解“惑”在何处,并剖析其带来的后果,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解惑之道。
“惑”在何处
中国国企的治理结构相比美国、德国等典型模式的治理结构要复杂的多。
美国模式的治理结构是一元制/单层制董事会模式:公司股东会下设董事会,并无独立于董事会的监事会,董事会同时具有决策权(战略决策)和监督权。美国外部独立董事的比例通常在2/3以上,这使得美国的董事会越来越偏重于监督,而不是决策,因为决策不是外部独立董事的优势,于是战略决策的拟定便交给了经理层,董事会主要负责战略决策的审议批准,并对战略决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但选聘CEO却是董事会的核心决策权力,是不会下移的。日常经营决策则完全授权经理层。
德国模式的治理结构为双层制董事会模式:公司股东会下设监督董事会(Supervisory Board)和执行董事会(Management Board),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监督董事会(由非执行董事组成,代表股东和员工利益),再由监督董事会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会(由执行董事组成),监督董事会为执行董事会的上位机关,对后者有很强的制约作用。这种双层治理结构严格遵循管理(执行)组织与监督组织分离的理念,要求监事(监督职能)与董事(执行职能)不得交叉任职。监督董事会通过任命、薪酬谈判、解雇包括总裁在内的执行董事会成员对其进行监督与约束,但无权直接参与公司管理。
中国普遍把德国的“监督董事会”简称为“监事会”,把“执行董事会”简称为“董事会”,这种简称使我们经常把德国的“监事会”和“董事会”误解为就和中国的监事会和董事会类似。其实,德国的双层制与美国的单层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却和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很大。德国双层制的监事会(即监督董事会)类似于美国单层制的董事会;德国双层制的董事会(即执行董事会)类似于美国单层制的经理层。二者的差别只是德国双层制的监督董事会的构成和执行董事会的委员会形式与美国单层制不同。单层制下的董事会构成以独立董事为主,经理层则是CEO拍板决策;而双层制下的监督董事会采取共同治理形式,体现在人员构成上,职工代表不低于1/3,其他为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代表,执行董事会作为经理层,采取委员会形式,总裁没有单层制下的CEO那么大的权力。
中国公司(含国有公司)在股东会(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平行机构,经理层由董事会选聘产生,董事会和经理层都接受监事会监督。但由于监事会在实践中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所以2023年新公司法已把监事会作为自选机构,如不设置监事会,则其监督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这意味着中国公司治理模式也正在向单层制趋同。除上述机构外,国企还设有党组织(不同国企称谓不同,以下统称“党委会”)。现有政策对党委会、董事会和经理层三个治理机构的定位分别是:党委会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促落实”是国企政策的表述,但《党章》的表述仍是之前的“保落实”);董事会定战略、做决策、防风险;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
现有政策对党委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职权定位看似清晰,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冲突:
(1)党委会“把方向、管大局”中的“方向”和“大局”如何界定?董事会负责定战略,而战略本就是方向性和大局性的问题,这使董事会定战略时容易产生困扰。
(2)党委会促落实是否包含促使公司战略决策的落实?而董事会监督经理层落实董事会批准的战略决策也是政策和法律规定的权力范畴,亦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规范,这在新公司法规定监督权可以交给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更是明白无误地确定了这一职权。2021年国务院国资委出台的《中央企业董事会工作规则》也把监督权赋予了董事会。可见,党委会和董事会在监督职权上出现了重叠。如果把党委会的“促落实”表述为“保落实”,则党委会的监督职权会进一步强化,其与董事会监督职权的重叠程度可能会更大。
(3)董事会做决策和防风险是否包括日常经营的决策和风险?而日常经营决策是经理层的法定权力,防范日常经营风险则是经理层的法定责任。这可能导致董事会对经理层产生越权行为。
显然,现行董事会的职权有的被弱化了,有的僭越了,加之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差异和混乱,导致企业在实践中难以清晰划定董事会职权的界区,但董事会的责任却很大,而且有进一步加大趋势,即使在其职权被弱化时,责任也不会被同步减弱。
另外,现有政策还强调“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即党委会部分成员进入董事会和经理层,董事会和经理层中的部分党员进入党委会,甚至有国企的经理班子全部进入党委会。这种政策的目的被认为有助于董事会和经理层贯彻党的意志,但由于职权交叉,在实践中却反而加剧了职权不清晰,进而导致监督失效。尤其在党委会与经理层二者重合度很高的情况下,党委会如何“促落实”?基于新公司法,如果不设监事会,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而董事会决策需前置到党委会讨论,党委会又与经理层高度重叠,此时不论是董事会还是党委会,都难以形成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从而极可能形成监督真空。
“惑”之后果
对于国企来说,从理论上,董事会是作为国有股东(即全体人民)的代理人而存在的。同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先进组织。这意味着,在国企中,从国有股东的代表主体来说,存在双重代理人,即党委会和董事会同时成为国有股东的代理人。
需要指出的是,领导理念和公司治理理念是有区别的。领导理念是一种管理理念,即“下级服从上级”;而公司治理理念是契约理念,强调不同主体在平等基础上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达成契约,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当领导理念和契约理念同处于同一治理体系中时,就可能出现如下问题:
(1)董事会职权难以清晰。现有政策和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会是最终的决策(指战略决策)主体,但并未明确,万一董事会的决策意见和党委会前置研究的意见不一致时,该如何处理?如果董事会发现党委会前置研究的意见存在瑕疵或问题,是否可以提请修改,或者提请重新研究?这一机制如果得不到明确,董事会职权的清晰化也就难以实现。
(2)合规风险。由于党委会与经理层的重合度很高,党委会前置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近乎经理层前置研究,如果董事会不敢否决党委会前置研究的意见,变成被动的程序执行者,这就与公司法关于董事会是最终决策者的法律定位的规定不一致,合规风险加大,这在海外国企中尤为突出。
(3)责任承担的“尴尬”。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不可能是党委会成员,如果绝对服从党委会的决策意见(对于拥有党员身份的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更可能如此),则只要决策错误或失误,则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必须自己承担责任,党委会不会代替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承担责任,这就出现职权与责任不一致的尴尬。对于担任党委委员的董事(内部董事),这种尴尬同样存在。
(4)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和海外资本。在混合所有制国企中,党委会和董事会在事实上的代表主体可能出现不一致。党委会倾向于代表国有资本或国有股东代表;董事会则代表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中的社会资本和海外资本。二者的不一致可能导致对社会资本和海外资本的吸引力下降。。
除了以上实践中看得见的问题外,还会增加无形的代理成本和剩余损失。由于“无形”,所以经常被忽视。国企党委会作为国家和人民的代理人,现有政策规定是通过董事会决策前置研究与监督经理层两种方式来参与国企治理的,然而这种独特的委托代理链条的存在,却可能导致党委会融入公司治理时产生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进而产生剩余损失。
其一,多设一条委托代理链条的治理机制设计本身会增加决策与监督成本。为了加大对代理人的监督力度,国企在组织机构设置和调整上会花费较多资源(包括内部和外部)。无论是决策权还是监督权,现有政策和法律均没有对党委会和董事会二者做出清晰划分。双重甚至多重的决策和监督提高了企业决策的错误率,过度复杂且职权边界模糊的治理结构又导致企业内部摩擦增多,这使得企业的决策成本和监督成本较大幅度上升,降低了决策和监督效率。
其二,治理主体职权边界模糊以及权责不一致进一步导致国企剩余损失上升。由于职权边界不清,而责任较大,出于规避责任的考虑,董事会在决策时往往偏于保守,比如有较大风险但一旦成功可以带来巨额收益的创新项目往往不敢做出决策;本已经过董事会授权的经理层日常决策仍要经过党委会前置研究,等等,这无疑都会贻误很多市场机会。另外,决策链条过长,重复决策,推诿和内耗严重,则导致企业无法适应随时变化的外部环境,也会错失发展良机。还有,董事(尤其是执行董事)任期随意性强,导致任期契约难以执行和落实,使得董事会治理不具可预期性和稳定性,从而难以做出长期的科学决策。
概括起来,国企剩余损失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任期契约的不完全性;二是代理人服从行政安排的决策行为;三是监督约束的边际成本大于实施监督约束能够产生的预期边际收益。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且都与行政干预的随意性和政策的不稳定性有很大关系。
基于以上原因,使得董事会作为代理人的实际决策与能够实现委托人(指作为国有最终股东的全体人民)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之间产生偏差,带来大量时间成本以及效率损失,从而产生剩余或福利损失。
总之,目前国企存在治理主体协同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各治理主体制度层面职权边界模糊以及权责不一致,并由此引发治理主体的决策冲突和重复,这会导致代理成本大幅上升,给委托人带来隐性福利损失,也使得本可以实现的国资增值不能实现,尤其是不能最大化实现。在严防国资流失的强压下,却造成实际上的巨额国资流失,作为最终股东(即全体人民)的福利最大化更难以实现。
如何解“惑”
解决国企董事会职权清单之“惑”,绝不能仅仅满足形式上的职权清单,更重要的是要注重能否在实践中落地,而能否在实践中落地,就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主要包括:
(1)董事会作为法定的决策和监督主体,制定董事会职权清单时应该坚持“职权唯一”、“权责统一”和 “职权法定”原则。“职权唯一性”是指董事会所拥有的决策权和监督权不能同时分割到其他主体,即不能与其他主体同时共享同一职权,否则就会形成职权交叉,行权时就会互相推诿和扯皮。因此,应该尽可能避免董事会与其他治理机构之间的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权责统一性”是指要保证董事会的职权与责任的统一,也即“董事会独立决策,独立监督,独立承担责任”。这里,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的独立性至关重要,所谓独立性是指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扰,否则,就谈不上担责,或者承担了与其职权不对称的责任,由此就会导致董事在行权时以自保为原则,而不是以科学和有效为原则。“职权法定”是指董事会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必须由法律(而不是政策)予以明确界定,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大幅提高决策和监督的可预期性。
(2)对于党委会前置研究的意见,法规中应该明确董事会享有否决权,以使董事会对所做决策真正独立负起责任来。根据公司法,董事会(有时是股东会)是公司战略决策的最终决定者,同时承担对所做决策及其落实的独立责任。由于新公司法已经实施,预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而由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来承接原监事会的职权,这意味着董事会需要具有更高的独立性,而董事会的独立性首先依赖于董事会主要由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构成。在这种情况下,决策的拟定将更多的由执行董事和高管承担,而董事会只是负责最终审议批准。由于经理层与党委会的重叠度很高,这种重叠又难以避免,而党委会成员和经理层成员都是公司内部人,他们对公司和市场的了解远胜于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因此,董事会决策前置到党委会进行讨论是很有必要的,这种讨论也主要是与经理层的讨论。其实,在发达国家,董事会决策前与经理层人员的交流和互动都是非常普遍的。因此,把董事会决策前置到党委会研究讨论,理解成董事会决策前与公司内部董事(主要是执行董事)和高管的充分交流和互动更为合适,因为这本就是董事会决策的正常程序。而过于强调党委会前置研究,可能会使董事会不敢否决党委会可能错误的研究结论,从而导致权责不统一。目前政策既然已经规定董事会决策必须经党委会前置研究,那就应该同时规定,当两者意见不一致时,应该如何按程序处理,从而明确董事会应享有的职权。
(3)严格落实任期制和契约制,以保证职权清单的可执行、可考核和完全落地。董事会任期制和契约制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契约通常是对董事一个任期的契约。没有任期制或任期很随意,则契约就难以履行和考核,契约就可能变得形同虚设,尤其对于长期或较长期的契约,就无法形成可预期性;反之,没有契约制,则任期就变得没有目标。目前国企董事和高管的任期比较随意,能够做满一个完整任期的董事和高管所占比例很低,这对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监督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国企的监管机构或股东单位应该尊重和严格落实对董事和高管的任期制和契约制,在任期结束前,除非能力低下或者渎职、犯罪,不得随意中断董事和高管的任期,年龄不应构成未满任期被免职的因素。
(4)应明确规定党委会代表所有股东,包括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而不应仅仅代表国有股东。既然《党章》明确规定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先进组织,全体人民无疑既包括国有股东,也包括非国有股东。严格意义上,非国有股东是内含在国有股东中的,但事实上,国有股东往往是狭义的,没有把非国有股东包括在内。因此,加强党在国企中的领导作用,应该是通过党的引领使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实现最终股东即全体人民福利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强化责任机制,既然党委会参与决策,那就必须要求包括党委会成员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要对自己的行为独立承担责任,要建立每个决策参与者的行为准则和备忘录,以便于明确责任或免责,保证所有参与者的权责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