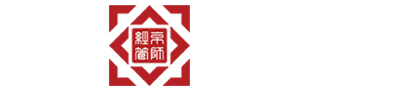百年变局在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东升西降”或“南起北伏”,即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断升高;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数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总产出中的占比也超过了发达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9年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世界GDP总额中占比为42.6%,发达国家为57.4%;到了2018年,发展中国家占比上升到59.2%,发达国家则下降到40.2%。在近20年时间里,发展中国家占比上升了17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上升0.9个百分点。如果这种趋势在未来继续延伸下去,那么,再过2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总产出占比将接近80%。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吗?
世界似乎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未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会继续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吗?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会不会出现变化?如果变化,会是什么情形?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业绩
世界银行在1977年约请一位经济学家大卫·莫拉维茨(David Morawetz)撰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二十五年”的文章,刊在《金融与发展》1977年9月号。这篇综述文章回顾了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业绩。它的基本概括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以1974年美元值为基数,在1950—1975年期间年均增长3.4%,同期发达国家为3.2%,两者相差不多;全部发展中国家人口在世界占比1953年为68.1%,1980年为73.6%,上升5.5个百分点;同时,发展中国家GNP在世界占比1955年为20.7%,1980年为21.5%,上升仅有0.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25年中,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NP占比的那一点点上升,主要由其人口增长所带来。
从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从事研究,努力为发展中国家寻找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到80年代中期,有学者认识到,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能不能自动获得“追赶”优势,国内制度结构等因素至关重要(Abramovitz,1986)。
80年代末以后,世界经济局势发生重要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逐渐呈现加速增长势头。从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开始,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开始高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优势”(按同期内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长率高于发达经济体的百分点来度量)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高峰。
图1显示1980—2019年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GDP增长率。两者皆有显著的年度波动。为缩小年度波动的干扰效应,图2取了两个指标的三年平均数。这样,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对比趋势:在80年代,两者增速几乎完全相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高于发达经济体仅0.08个百分点);90年代,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高于发达经济体(0.85个百分点);20世纪第一个十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优势”达到高峰(4.25个百分点);在第二个十年中,发展中经济体继续享受“增速优势”,但两者差距相对于前一个十年已有缩小(3.09个百分点)。
发展中国家获得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优势,为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命运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性机遇。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是百年变局在经济上的最大体现。
展望未来,例如展望下一个十年,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增速优势”会有何种变化?是继续维持3-4个百分点的增速优势还是降低到1-2个百分点甚至两者回归到80年代的情形,增速几乎完全相同?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优势的重要因素。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优势的三大因素及其变化趋势
很容易看出,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所获得的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优势,在时间上正好与经济全球化高度吻合。这20年也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其标志是冷战结束,各国经济竞相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得到加速增长,等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但是,从本文的角度看,肯定有一些“特别的因素”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受益程度大于发达国家。可以认为资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进口需求扩张和跨境资本流动就是属于这种“特别的因素”,它们不仅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给发达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效益,而且更多地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重要的经济增长效益,尤其给那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加显著的效益。
(一)资源价格变动趋势
图3显示世界粮食价格和原油价格在1980—2019年期间的表现。其中,在1980—1999年期间,世界粮食价格和原油价格的基本趋势是下降和处于相对低位;在2000—2012年期间,世界粮食价格和原油价格几乎直线上涨,仅在2008—2009年期间出现过短暂性暴跌;在2013—2019年期间,世界粮价和油价转为下行,但其水平高于它们在1980—1999年期间的平均水平。
粮价和油价的上涨会让粮食和原油的主要出产国和出口国获得较多效益。它们中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相对多一些,尤其在近些年北美发达国家大量出产页岩油气之前。未来,在粮价和油价继续处于21世纪以来的低位时,这意味着那些大量出产和出口粮食和原油的发展中国家,将不再能像以前那样获得特别的或额外的经济增长效益了。
(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
资源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国家拥有广袤土地和丰富的矿物储藏,有的国家则以人口众多、耕地相对紧张而闻名。对那些劳动力充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积极发展外向型的出口导向产业,是提升经济增速并获得额外效益的可行途径。60年代后半期在东亚出现的“四小龙”或“四小虎”经济增长奇迹,为后来的许多国家都提供了这方面的示范作用。但出口导向的政策需要有外部市场的支持,而这通常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的开放和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市场要么体量不够大,要么不够开放。对积极发展制成品出口产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货物进口需求就成为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了。
图4比较了1980—2019年发达国家在四个时期中的GDP增长率和货物进口增长率。在其中四个时期中,发达国家货物进口增长率都显著高于GDP增长率,这不仅体现了它们的对外市场开放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即它们国内市场的外向性提高了。在80年代(1980—1989年),发达国家货物年均进口增长率为5.2%,GDP增长率为3.1%,前者为后者的1.7倍;在1990—1999年期间,这两个指标的倍数上升到2.6;此后,在21世纪的两个十年中,该倍数降低到2.0和2.1,依然高于80年代的水平。
前面已经指出,在1990—2019年这30年期间,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时期,也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但是,随着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近年来的一些变化,尤其是疫情以来各国经济政策更多地转向了本土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发达国家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程度在未来很有可能出现降低。它们很可能会对有关的贸易政策或市场进入政策进行限制性的调整。这样一来,那些已经高度依赖发达国家进口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将多少会受到一些不利影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享受额外的效益了。
(三)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跨境资本流动加速增长。图5显示,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流出额在1970—1979年期间平均每年为279.3亿美元,在1980—1989年期间平均每年为880亿美元,在1990—1999年期间为3728.8亿美元,在2000—2009年期间为9356.1亿美元。在这40年期间,每过十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年均额就翻番,增长速度在20世纪最后十年达到高峰(翻了两番)。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既流向其他发达国家,也流向发展中国家。在1990—2009年这20年中,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以前大大增多了。而且,很重要的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帮助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升自己的制造能力,得到了设备更新和组织管理变革的催化剂。
但是,我们从图5也看到,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年均流出额在2010—2019年仅比前一个十年略有增加,为9805.5亿美元。这个数字的变化,或许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还在继续中,但它的加速增长的势头却弱化了。在下一个十年,即2020—2029年中,这个数字甚至有可能出现减少。而且,跨境直接投资流动的变化不仅会表现在总量水平上,也可能表现在区域流向构成上。
三、疫情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次调整其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表1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7月三次有关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09年GDP增速的预测,以及后来得到的它们2009年GDP增速的实际数。我们从表中可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GDP增速与发达国家之差(前者高于后者的百分点)的预测,从2008年11月的5.4上升到2009年7月的8.9,呈现直线上调趋势;实际结果是,2009年发展中国家GDP增速高于发达国家6.1个百分点。可以认为,2008—2009年那场国际金融危机给发达国家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优势在危机中凸显出来。
但是,联系我们在第一节的讨论也可以看到,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给予发展中国家GDP增速优势的有利作用是短暂的,没有能够持久。如前指出,在2000—2009年期间,发展中国家GDP增速高于发达国家4.25个百分点,而在2010—2019年期间,这个增速优势下降到3.09个百分点,比前一个十年水平低了1.14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说,发生在这两个十年时间段之间的国际金融危机没有能够阻止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优势的缩减。
2020年初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再次提出了疫情会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两大板块经济增长前景的问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许多机构和人士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弱于发达国家,面对疫情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能会显现出较多的脆弱性。或许正是因为受到了这种想法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的数次预测中,连续下调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在2020和2021年的预测结果(表2)。关于2020年的GDP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上半年(即2020年1月、4月和6月)的3次预测中,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会高于发达国家至少5个百分点,因为那时疫情的发生地主要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到病毒感染的人口数量相对少。但在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度下调了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GDP增速预测数,其与发达国家GDP增速之差降低到2.5个百分点。
从表2中还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下调了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的GDP增速预测,而且也下调了它们在2021年的GDP增速,以及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GDP增速优势。后者从2020年初的3个百分点下降到10月的2.1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在2020年7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特别指出,新冠疫情(COVID-19)带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妨碍它们与发达经济体的趋同性(Dieppe 2020,第四章;也参见Economist 2020)。
从短期观点看,各国经济遭受疫情冲击的程度首先取决于病毒扩散的程度(人口感染面积)和封闭措施的直接效应;其次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再次取决于各国经济结构的有关特点,例如旅游业和服务业的重要性(旅游业和其他普通服务业被认为会受到疫情较大的冲击)、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等等。单就这些情况来看,目前还很难判断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什么或有多少不同之处。当然,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疫苗普及率会高于发展中国家,其数字化程度也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许多发达国家人口密集程度和聚集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前者的人口感染率也显著高于后者。由此,发达国家实行“封闭”措施的范围和时间长度大于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也因此受到较大不利影响。目前显然还难以判断在短期内,例如在2020年和2021年内,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谁将受到疫情较多的不利影响。
就疫情的长期影响而言,如果疫情在未来一两年内得到控制,它的短期影响将随之消退,剩下的就主要是长期影响了。在这方面,疫情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将在未来数年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而这就可视为疫情的长期经济影响。
第一件事情是国际供应链的地理调整。疫情期间,经济民族主义和产业保护呼声在许多发达国家进一步加重或上升了。疫情结束后,一些发达国家会针对国际供应链进行一些调整,包括将一些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回迁或迁往别处。如果供应链或产业链向发达国家回流,这将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关系,也会涉及到前面(第二节)说到的两者之间的直接投资流动。如前所说,这样的事情总体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供应链的调整主要发生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即工厂搬迁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另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而主要影响到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相互差别。
疫情期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大大增加了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使用,包括扩大财政开支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等,它们给各国都带来了债务率上升的居民,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还特别地带来了外债的增加。这样,在后疫情时期,各国都将面临债务风险,尤其是政府部门债务风险。问题在于,各国应对债务风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应对债务风险的能力低于发达国家,尽管后者的债务率在疫情以前和疫情期间都显著高于前者。
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实行了扩张型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现了政府债务率急剧上升的情形。后来的情况表明,是那些应对债务风险能力较弱的发达国家——例如希腊和冰岛等,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而已经背负很高债务率的国家——例如日本和美国,却因其较高的应对能力而避免了债务危机。从这个观点看,在未来后疫情时期,一些政府债务水平在疫情期间大幅度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或将遭遇新的债务危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后疫情时期,债务率上升带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将大于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程度。也就是说,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对经济增速的未来趋势而言,疫情带来的影响对前者是客观上不利的。
四、未来分化的可能性
疫情发生以来,一些人士开始谈论“K”型增长趋势,即不同国家可能出现差别显著的经济增长态势:有的走向复苏或快速复苏,有的停留在低迷状态,迟迟不能转为复苏;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里面,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里面。“K”意味着分化,即经济增速的显著差别。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研究经济发展的许多成果都认为,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位居前列的国家通常都具有若干共同特征,包括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并具有弹性、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发展、经济政策相对稳健和平衡,等等;而那些长期不发展或在发展过程中不时大起大落的国家,则具有或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政治制度不稳定、政局和政策多变、产权保护微弱、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充分、国内金融市场有缺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基础构架不牢固,等等。早在21世纪初,就有研究者概括说,各国经济增长问题的众多研究者,前前后后考察过多达145个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说举不胜举(Durlauf, Johnson and Temple 2004)。
在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发展中国家那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许多积极有利的因素,可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相对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国内因素的要求。在全球化进程受到一定挫折的后疫情时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虽然继续有一些积极有利的因素,但消极不利的因素也显著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对国内因素的要求就提升了。这也就是说,未来,在后疫情时期,发展中国家将需要更多地利用国内因素来支持和提升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让国内因素发挥较大的作用。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各自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经济政策方式和稳健性等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别,“让国内因素发挥较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让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差别日益凸显。这也意味着,在未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相互间将出现比以前时期更加明显的差别,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分化将可能是一种趋势。
五、结论与展望
前面第一节的基本看法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获得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速优势,这种优势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2000—2009年)达到高峰。发展中国家获得相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优势,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命运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展望未来,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趋势是不是会继续下去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延续。
前面第二节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0年(1990—2009年)时期中,有三大因素支持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高于发达国家。这三大因素是:国际资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市场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跨境直接投资流动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
或许,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三个因素分别称之为经济全球化在那个20年带给发展中国家的“价格红利”“市场需求红利”和“资本红利”。发达国家也从中享受到经济效益,但发展中国家从中享受到较多的经济效益,故而发展中国家得到了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
如果这个看法成立,那么可以推论说,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发展中国家大于发达国家,而如果出现经济全球化逆转,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地方,发展中国家亦多于发达国家。
在20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之际,以下几个趋势性变化将有很大可能性。一是油气等在内的资源价格将因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而停止上涨,尽管不能排除其短期波动。二是发达经济体倾向于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其中一些也会较多地转向“选择性多边主义”,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待遇上享受搭乘免费快车的便利减少。三是国际直接投资增长势头减弱,尤其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难以再像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那时的热潮景象。
概括地说,许多发达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会转向“内向化”发展,即相对减少外部供给来源的依赖以及向外输出资本和技术等。这些动向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以来已经显露,但在2020年暴发新冠疫情以后似有进一步加重的迹象。也即是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在未来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将增多一些不利因素。
以此判断来推测未来世界经济两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我们可以认为它们之间的GDP增速将愈益相互接近。
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增长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因素的支持,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别也会较以前时期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的变动,势必给国内因素带来较多的和新的压力。因此,未来,发展中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大国内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释放和增强国内经济活力,深度拓展国内市场;同时,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更加有效地利用外部经济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环境变化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此,中国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思路很有战略意义。这个思路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在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际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也指出了经济政策发力的重点将偏向国内市场。这也是对国内改革和开放方针的一个新定位。在新方针指导下,国内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将会摆在更高的位置,内源性经济增长将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也将得到新的发展和调整。
来源:《开放导报》,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