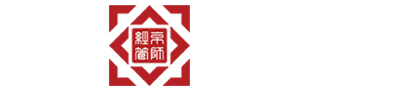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目前还只是处于萌芽之中,没有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不可能有所成就。最近,有的人排斥使用“本土管理研究”这个概念,有的人觉得关于“本土管理研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是,我觉得,相比舶来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对于本土管理研究方面的鼓与呼还太微弱,还没有形成气候,还不够百花齐放,多姿多彩。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的贾旭东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统计,2006-2016年之间,中国管理学者发表论文93000篇左右,其中以扎根理论做的研究大约只有140篇左右。如果再加上英文论文,估计这个比例更低,不到0.1%。由此可见,在中国管理学界要想推进多元典范是何其艰难的事情,更何况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学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其难度之高,可想而知。
一百年前王国维先生的观点给所有有志于推进本土管理学研究的学者可以有一点借鉴和启发。王国维说“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事实上此说已开中国哲学研究必须借鉴西方哲学之“形式系统”的先河。王国维又说:“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5页),又说:“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同上书,第71页)。
事实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想推进自己的本土社会科学研究,不管是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抑或哲学等,都面临着相似的难题和挑战,必须有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是一孔之陋儒。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有深厚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独特国情。大国就应该有大国风范,我们必须建立学术自信和自主的社会科学,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
但是,如何具体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管理学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如果这个问题无法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那么各种呼吁、感叹、情怀和姿态就无法吸引更多年轻的学者走上这条荆棘丛生、前途未卜的学术冒险之旅。
我个人“凭空设想”一下,至少有这样几条道路是可以尝试的。
第一,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本的世界观和个人价值判断的标准,指引自己进行管理学理论构建和经验研究,颠覆西方管理学中内隐的价值取向。只有彻底质疑西方管理学背后的核心文化假设(理性客观、分析导向、价值无涉、更快更高更强更多、战胜他人、结果导向等),我们才能彻底摆脱西方管理学对我们不自觉的影响和控制。例如,我们能不能基于道家哲学的“知足”提出“适度营销”的概念?而不是一味鼓励公司制造地更多,销售得更多,顾客购买得更多?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双11”这样的狂欢提出管理学者的独立批评。我们能不能基于儒家的“修身、齐家、平天下”提出领导力自我发展的修养理论?走这条路,需要学者具有极大的文化自信和自觉,需要有“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学术视野,需要有宇宙关怀。难吗?说难也难,也不一定,主要看一个人的境界和见识。
第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一分为三”和五行等概念当作理论建构的工具(theorizing tool),结合西方管理学中比较成熟的成双成对的概念,建立更加整合性的理论。例如,我做过的一个研究中,就是采用“阴阳”和“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把它们作为理论建构的工具和视角,用来重新梳理西方跨文化研究中的相关文献,重新厘定JIBS上中争论了很久的GLOBE研究中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习俗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赵向阳,李海,余佳,2014)。我个人认为这个研究是我做过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之一。类似的,在西方的关于悖论研究中,Poole和Van de Ven(1989)和Schad, Lewis, Raisch & Smith(2016)的文章中都鼓励大家把悖论当作一个元理论或者进行理论建构的工具(Paradox as a meta-theory and theorizing tool)。
走这条道路,切记不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一个大帽子、一个“垃圾桶”,看见任何管理现象都说它是“阴阳”,都说它是“一分为三”,都往里面放,久而久之,只会引起条件反射式的反感和排斥。因为“阴阳”这个概念是中国文化中的根源性比喻(Root metaphor),它是普适的,无法证伪。卡尔·波普认为:绝对正确并不是科学理论的优点,相反,它反倒是一个理论的致命弱点。一个学说之所以绝对无误,并不是因为它表达了确实可靠的真理,而是因为经验事实无法反驳它,阴阳这个概念就是如此。我建议,最好把阴阳、一分为三、五行等静静地嵌入到自己所构建的具体的理论和模型中去,作为逻辑内核,而不用过分强调和凸显。这种传统文化和管理学经验研究的水乳交融,最妙。例如,黄光国教授所建构的“人情-面子理论模型”(Hwang,1987)和“自我的曼陀罗模型”(Hwang,2011)采用的事实上就是这种内嵌式的理论建构方法,其中阴阳套着阴阳,但是,用不着点破。
第三、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概念,例如,人情、面子、关系等。这几个概念也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管理学者贡献最著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两条路最好别走。第一条路是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例如,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交易成本理论等)来解释这些概念,你会发现别人的理论很丰富,该有的都有了,所以,中国的“人情、面子、关系”毫无本质上的特殊之处,最多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第二条路是简单借用中国传统文化来重新解释这些概念在管理学中的应用。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活在当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活在文化典籍的修辞中,这是一个问题。而且简单地借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当下的管理实践,很可能厚古薄今,而且远离了管理学经验研究所要求的具体性和情境性,会让人觉得大而化之,不够接地气。
社会学家翟学伟教授建议最好采用“非中非西”的方法(翟学伟,2016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煮茶问道”演讲PPT),从当下的生活世界出发,紧扣鲜活的生活现象案例,从下而上,叠屋架构出一套与经验世界紧密相关的概念体系,最后接触到文化和哲学的层面,接触到东西方文化差异。对此,我非常认同。但是,这条路非常难走,可以说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两边都是悬崖,一不小心,要么落入西方理论体系的窠臼中出不来,要么落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酱缸”中出不来,无法挖掘出“中国之为中国,当下之为当下,管理之为管理”的真正特点来,同样也出不来好的理论成果。走这条路的学者,一定要融会东西,知己知彼,而且要有很好的平衡感。
第四、本土概念+西方方法+当下问题。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借用西方科学中最强大的方法论(methodology)和方法(method),也就是工具理性,来对一些本土概念进行研究。例如,营销学的第一位长江学者周南老师自己参与的一些研究中有不少都是采用这种模式,而且做得很好。例如《企业家公德和私德行为的消费者反应:差序格局的文化影响》(童泽林、黄静等,2015)、《消费者对品牌慈善地域不一致行为的负面评价及其扭转机制》(童泽林、王新刚等,2016)、《企业家违情与违法行为对品牌形象的影响》(黄静,王新刚等,2010)等,这几个经验研究都采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但是,都纳入了一些很本土的概念,都发表在《管理世界》,而且有启发性,足以说明这条道路是可行的,大家可以一试。
不过,走这条道路,有拼凑的嫌疑,尤其可能无法真正捕捉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韵。特别是在测量构念的时候,最好不要采用问卷和量表来测量那些难以测量的复杂概念,例如,悟、中道、阴阳辩证思维等。如果非得要测量,建议采用半结构化访谈,而且是基于具体情境,最好要结合专家判断。
第五,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反思一下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尤其是对“科学方法”的执迷不悟。中国管理学界的绝大多数人,从来不会把小说、诗歌、历史、修辞学、哲学思辨等纳入到管理学的常规研究方法中。事实上,西方主流管理学向自然科学学习的时间太久了,迷失了管理学之为管理学的本质特点(例如,复杂微妙的情境化、自反性、目的性、启发和教化、主动建构商业规律等),只有那些管理学中的大师,例如,德鲁克,马奇,明兹伯格等才敢于尝试那些被认为是旁门左道的表达方式,如小说、诗歌和哲学思辨等。国内的学者中周长辉教授的诗歌创作虽然经常紧跟管理实践中的热点现象,但是,被认为只是“业余爱好”,而刘文瑞老师对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系统性梳理,也只被认为是“敲边鼓”。
事实上,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大张旗鼓地提出,“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三种重要研究方法就是艺术、历史和修辞或者哲学思辨。诠释学的广阔视野是我们这些深受实证主义经验研究桎梏的人难以接受的,但是,已经成为了西方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力量。只要我们大家能对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方法”(例如,诠释、叙事、批判等)稍微有所了解,如果我们能从对“科学方法”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悟”、禅修中的本质直观、堆积如山的历史典籍、繁花似锦的诗歌等,都是中国管理学者重要的智慧资源,都是我们探究管理之道的重要方法。《管理学报》有一天会发表纯粹的诗歌体的文章吗?《管理世界》有一天会发表管理小说吗?中国管理学者能用戏剧或者电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吗?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把这些都看作中国管理学界成人礼的试金石。
我个人坚信,至少以上五条道路是可以尝试的,而且会让中国管理学变得更好。
来源:《管理学报》,2017年第1期“煮茶问道·本土管理研究论坛”,在本专栏发表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