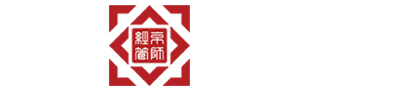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公布,这为中国企业家健康成长、充分发挥企业家能力创造了契机。对于中国企业,最关键的是要培育企业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机制,以最大可能调动企业家的最大潜能,进而才能实现资本的最大化增值。
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处于偏低水平
何谓企业家?熊彼特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企业家就是创新者。作为创新者,企业家必须具有创新能力。那么,如何界定企业家能力?借鉴国际先进的评价标准、基于中国国情、着眼于推动职业经理人市场,企业家能力应该包括四个方面,即企业家人力资本、关系网络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和战略领导能力。
对于一个特定企业,企业家是一个群体。为了了解中国企业家能力现状,必须对企业家能力作出评估,而要评估,就必须瞄准一个特定的创新者。无疑,这个创新者应该是企业的领袖。在现实的企业中,企业的领袖一般有两个人选,或者是董事长,或者是总经理(或称总裁,或称CEO),那么选择哪一个来评价?答案应是总经理,原因在于:很多人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能误解了,从规范的公司治理角度,董事长是董事会的召集人,不是公司的“一把手”;总经理则是经营层的行政首脑,是创新的第一担当者,因此,中国企业要长久保持创新活力,就必须高度重视总经理的能动性。
上市公司是企业的典型代表,我们从人力资本、关系网络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和战略领导能力四个维度设计了31个二级指标,计算了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一直处于偏低水平。2011 年、2013年、2015年和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均值分别为35.71分、34.81分、34.19分和30.74分,处于连续下降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战略领导能力和关系网络能力拉低了总体指数,前两者近几年均徘徊在30分左右,而关系网络能力更是在2016年降到了6分以下。近几年由于强力反腐,确实直接影响到了企业家关系网络的建立,也意味着之前的企业家关系网络存在着较多的畸形政商关联因素。企业家关系网络并非一定会带来畸形的政商关联,需要正确处理,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其实,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和战略领导能力偏低是更应该引起反思的,尤其是战略领导能力。
三个因素阻碍中国企业家能力发挥
目前看,阻碍中国企业家能力发挥作用的因素有三个。
企业家选聘市场化程度很低。根据我们的统计,2013年、2015年和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由市场选聘的比例分别是12.17%、12.12%和9.44%,呈连续下降态势。其中非国有控股公司总经理由市场选聘的比例分别是11.92%、14.47%和11.26%;国有控股公司分别是12.56%、8.41%和6.22%,比非国有控股公司下降更加明显。对于国有企业,目前企业家选择普遍采用任命制,而任命制的等级制很严格,企业家潜能难以发挥。一方面,国有企业董事会并没有独立选聘以总经理为首的高管的权力。企业家是需要创新的群体,创新必须有足够的动力,企业家创新动力来自淘汰机制,而淘汰机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独立的董事会独立选聘企业家的市场化机制,而国有企业恰恰缺失这种机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还没有摆脱行政干部的选拔体制,同时造成国企高管身份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性。即便是高能力的企业家进入国有企业,由于体制机制的束缚,也未必能更好地发挥其创新潜能。另一方面,经理人市场的缺失,也使国有企业不想、不愿通过市场选择经理人,因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还不想放权;也不敢进行市场选择,因为它们不相信市场,这些因素又更不利于经理人市场的建立。对于非国有企业,也具有类似的情况,浓厚的家族或创业者色彩,加之缺乏透明的经理人市场,造成较严重的个人权威主义,这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薪酬激励力度过低,使得经营者动力不足。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中。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普遍采取了一刀切式的降薪政策,不仅使动力不足问题更加突出,而且人才流失开始凸显。我们在考虑高管贡献的基础上,计算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即高管薪酬与其贡献的吻合度),2012年、2015年和2016年,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均值分别是71.38分、75.99分和138.47分,而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均值则分别是172.97分、461.35和485.14分,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大大低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这是造成国企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近几年国企高管的薪酬指数一直上升,但是他们的薪酬绝对额却在下降。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差?高管薪酬指数反映的是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吻合度,薪酬指数上升,而薪酬绝对额下降,这反映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由于近几年国企高管的普遍降薪,导致了公司业绩的更大幅度的下滑。这话反过来说,就是高管薪酬激励的适度增长,会带来公司业绩的更大幅度增长。这需要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
不合理的政商关系对企业家能力的作用发挥造成负面影响。第一,公司治理的官僚化或行政化。由于制度不健全,信息不透明,企业家为了项目的审批及各种信贷资源的获得主动向政府官员寻租。企业家为寻求和维持与官员的特殊利益关系,不仅要耗费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有的甚至成为政治人物的附庸,还要承担官员失势的风险,这不仅无助于企业家能力的提升,还使得企业家能力向非生产活动方向配置,并且会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挤出效应”,即使企业获得了一些关键资源也会将其用于短期获利较大的项目,而不是用于高风险性的创新活动,企业最终会丧失核心竞争力。第二,政府官员在财政分权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自主裁量权变大,在权力监督较弱的地区,政府官员可能在项目审批等种种环节“设租”,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家能力的错配。为了企业创新不受干扰,企业家往往不得不服从于各种“潜规则”, 这不仅会延缓企业创新的进程,使得不确定性增加,还有可能因涉嫌“行贿”而蒙受声誉损失,企业将会用获得的利润来弥补这种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高额成本,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加,最终企业的创新收益减少,由此,吸引企业家创新的门槛变高,造成企业家创新动力不足。
总之,一方面,经理人市场不健全以及董事会不能独立选聘总经理,或者任命制主导下的企业家选拨,难以选择到有能力的企业家,会埋没很多的优秀企业家人才;另一方面,现有激励和约束制度、总经理的附属角色、错位的政商关系,使得企业家的潜能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或者发生错配。
如何激发出企业家的最大潜能?
发挥中国企业家最大潜能,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
积极推动建立经理人市场。经理人市场的核心功能就是选择企业家,激发企业家精神,因此,政府加大力度建立透明的、职业化的经理人市场,对于企业选择到高度诚信的、有能力的企业家至关重要。对于国有企业(主要指竞争性国有企业),其与非国有企业一样,都要追求资本回报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应在保证国有资本监督权的前提下,充分放权,由董事会通过经理人市场独立选择高能力的企业家。选聘不同背景的企业家,包括选择成功的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会带来多元化模式和思路的优势,从而推进企业改革和创新。经理人市场成熟的标志是健全的诚信体系,以及透明的经理人信息披露,在此前提下,市场化选聘的标准是被选择的企业家如何在合乎公司治理规范和诚实守信的前提下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探索有效的企业家自我约束机制。一是落实责任机制。要划清各位董事,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权责边界。对于前者,要通过实施董事会备忘录制度,把董事会责任明晰到个人,对于失职造成损失者,给予足够力度的惩罚;对于后者,要明确董事长是董事会的召集人,而非公司“一把手”,确立总经理在经营层的权威和“一把手”地位,法无授权任何人(包括董事长)不得干预总经理的日常经营决策,同时总经理必须对公司日常经营决策承担独立法律责任。二是建立激励机制。要实现贡献与激励的有效结合。要在对高管贡献做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市场规则,给予与其贡献相吻合的物质激励和声誉激励。高管的贡献应以公司绩效和经营风险作为评价标准,以促进企业高管以一定的经营风险,创造尽可能高的经营绩效。责任清晰且失职处罚的力度大,能使企业家犯错和违规的成本极大提高;激励力度大,则会使企业家做不好的损失太大,或者说做好的收益很大。通过这样的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可以实现企业家的自我约束,而自我约束无疑会大大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要建立反腐长效机制,重构新型政商关系。一方面,要通过压缩公权力,切断企业家寻租的通道,增加企业利用政治资源的成本,让企业家能力更多地用于企业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将反腐败长期化、制度化,要提高官商勾结和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加大对官商勾结和腐败的惩罚力度,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实现依法治企,而依法治企的实质是强化公司治理规范化。中国公司治理的不规范,尤其是政府介入公司治理的错位,导致了中国畸形的政商关系,而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又是官商勾结和腐败的温床。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既要充分调动各类股东和董事会监督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前者是治理主体,后者是治理客体,二者必须有明确的区分。
来源:《董事会》,2017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