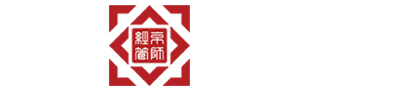一、历史回顾:从“市场化改革”大路径看“全面深化改革”三年走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新时代,期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重点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边缘突破外围启动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引“包”字进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首轮试水阶段,后来又在“艰难困苦”中熬过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旧体制回归复辟、改革开放停滞时期,终于在1992年“南巡”的春风吹动下,又进入新一轮以“市场化改革”为基本取向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进入21世纪,前期在“非零和博弈”状态下实施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双轨渐进式改革”之正面效应趋近于零,其所造成的权贵利益集团“体制内外通吃”、人民群众对改革成果少有“获得感”的负面效应日趋显露,在“零和博弈”状态下拿出“壮士断腕”魄力大刀阔斧进行“非帕累托改进”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危机四伏。
在这样“改革开放”何去何从、生死攸关的重要历史关头,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坚定不移高举起“改革开放”大旗,适时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集结号”,高屋建瓴进行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总部署,不仅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强调了沿袭“市场化改革”基本取向———“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而且高瞻远瞩地指出新一轮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面深化改革”三年多来,中央号角阵阵、步步为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改革与法治相向而行、破立并举、相得益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新发展理念布局‘十三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奏响了改革与发展的‘双重奏’;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新部署,开启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征程。”从总体走势来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大脉络日益清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面发力,各领域标志性、支柱性改革基本推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
简言之,从近40年“改革开放”大的历史脉络来看,以市场化改革为主轴,全面顾及十六大领域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自上“顶层设计”、而下“贯彻落地”为基本策略渐次展开,似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正拔地而起”。
二、现实挑战:“顶层设计”已完成,“贯彻落地”是关键,“上下互动”定成败
回看“全面深化改革”三年,从“2014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到“2015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年”,再到“2016全面改革攻坚年”,从统计数据来看,可谓硕果累累。特别是刚刚过去的一年,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各项改革任务进展总体顺利:领导小组共召开了12次会议,审议了146个重大改革文件,确定的97个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和128个其他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94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改革方案419个;国务院发布有关简政放权法规、文件28个,已经分9批取消下放国务院部门审批618项;供给侧改革成果显著,去产能(钢铁)6500万吨,降成本10000亿元,补短板(棚户区改造及公租房基建)658万套……{3}但是,“无数次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革别人的命、动别人的‘奶酪’易;革自己的命、动自己的‘奶酪’痛”,种种迹象表明,已经出现了“改革成就的书面总结‘成果丰硕’,但群众对改革成果的感受与期待仍存差距”的情况,“现实经济生活中仍遗存着某些计划体制‘特权’烙印,破坏了应有的市场秩序,阻碍了公平竞争和市场效率,成为障碍全面深化改革的阻力”,“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害怕担责,躲着走,拖着看,不敢碰硬”,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存在“不想为、不敢为、不会为”的现象。{4}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形势严峻,前面的路险滩不断、困难重重,任重道远。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全面深化改革”虽然已经成为中央的既定方针,但从舆论导向、干部认知及民众心态上,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远没有在上上下下、上下贯通的意义上达成普遍共识,更未在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意义上真正形成如当年“南巡”那样雷厉风行、席卷全国的充分思想准备和锐意改革新气象。就中央高层而言,高屋建瓴、顺应世界潮流,早已将“改革开放”看作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但由于缺乏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张旗鼓全面系统动员,加上左右摇摆、前后暧昧的多重信号相互干扰,在改革问题上没能真正触及中下层领导干部及普通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从而导致不少领域、地区、单位各层级干部群众普遍存在“不想为、不敢为”的现象,特别是“零容忍反腐败”的高压环境下,一些领导干部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改革得罪人,没有好下场;宁可不改革,只要不犯错”的心理普遍存在,“上有积极政策,下有消极对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导致全面深化改革落地实施缺乏给力的“动力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在“面”上千头万绪,而且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中央早已部署了“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但怎么在操作层面聚集成“落地有声、有板有眼”的改革举措,还大成问题。2017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要统筹协调各方面改革工作,增强改革定力,加强改革协同,完善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和办法,把责任压实、要求提实、考核抓实,推动改革落地见效”,中央明确要求“改革工作要突出重点、攻克难点。要加强对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对外开放等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推进,抓好已出台改革方案的落地生根”。但是,改革,特别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说到底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博弈均衡,不仅要靠“自下而上”单向发动,更要依赖“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如果没有一种基于“共同愿景”且“取向明确”的上下协力,特别是“外围突破,边际调整,循序渐进”的迂回策略,试图“眉毛胡子一把抓”、面面俱到、齐头并进,一厢情愿地要坚持所谓“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跟着问题走,哪里出现新问题,改革就跟进到哪里”,甚至沿袭传统“一刀切、大一统”行政指令性计划做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改革落实上投入更大精力,要建立抓落实的台账,要有硬任务、硬指标、硬考核,每项改革落实要有时间表、路线图,跑表计时,到点验收。要落实责任,地方和部门一把手要把抓落实的责任扛起来”,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大多数的情况必然是“雷声大、雨点小”,落而不实、收效甚微。常言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改革、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无论在“目标导向”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必须突出一个“放”字,而且要做到“知行合一”地开“放”,从现实情况及事后观察结果来看,不容乐观。比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既然明确了“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与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产权制度原则,那么在实际公司治理及政府规制行为上,就需要首先给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公私平起平坐,彼此互不侵犯”具体制度安排,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之前,就急匆匆搞所谓“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到头来只能是“公吃私,一锅粥,不清不楚瞎折腾”;同样道理,没有“开放”或“放开”做先导,没有切实保障“百花齐放、百花齐放”、“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具体制度安排,要全面深化文化科技体制改革、社会制度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法治中国”,从实操层面来看,往往事与愿违,最终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难点及成败关键点,不在“面”上而是在“深”字上,即如何“以迅雷不可掩耳之势”尽快突破长期以来日积月累盘根错节形成的行政性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生态链条,为此,显而易见,以“政府职能及角色转变”为基本取向、以“缩减官僚规模、限制行政权力”基本举措的行政体制改革,乃2017年及后续若干年内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中之重”。关于“深化”改革重点,虽然在顶层设计中,也已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这里的话说得似乎有些“暧昧”:其实,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就“改革”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件事情上,“政府”处于有绝对优势、决定性作用的主动方,而“市场”则是被动、非决定性和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的一方,如果政府不积极主动“自我革命”,看重并固守“既得利益”还时不时地“千方百计”强化其已有行政性垄断权力,不仅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往往越界、错位、扭曲地发挥其作用,那么,“市场化”改革就看不到任何希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必然沦为一句空话。在双轨制长期渐进并存的过程中,传统行政指令性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各种政府行政性垄断“特权”,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一些部门逐渐滋生了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权钱交易”生态链,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这早已成为屏蔽阻挠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直接障碍和最大阻力。大家有目共睹,多少年来,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的所谓“民生”问题,说到底都是“民权”问题,诸如“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等人民群众缺乏“发展成果获得感”的领域,恰恰都是因为行政性垄断权力长期固守、市场化改革严重停止、远不到位的领域,这也是腐败丛生、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最损害政府公信力和执政党现象的领域。
说来说去,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沿着改革开放路径回头看,还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向前看,“市场化”依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取向,而打破行政性垄断,“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切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关键及重中之重。
三、对策建议:高举市场化改革大旗,大刀阔斧聚焦行政体制改革
其一,在“主导方向”及“舆论导向”上,自上而下应该高度珍惜并认真总结汲取近40年“改革开放”丰富成果及经验教训,进一步在全国范围、举国上下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旗帜鲜明地亮出“市场化改革取向论”和“全面深化改革中心论”,毫不含糊地以“制度创新”为主题主线的改革作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永久推动力。在这方面,深圳作为当年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特区,应该说有着独一无二的“优良传统”、“历史先机”和“地缘优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应该进一步“锐意进取,解放思想”率先走在最前沿,很好发挥“掀改革春风沐浴全国”的先导引领作用。
其二,要重提“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放”字当头,将开放搞活、放开放松并尽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管制模式,作为启动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龙头”。改革有风险,改革者要担责任,如果改革者面临的政策环境是一种“个人无限责任,改革没有好下场”的负激励导向,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改革发生,更不要说“全面深化改革”了。特别是改革已经进入进退维谷、风生水起的攻坚战状态,欲将改革不断推向纵深并取得关键性突破,就需要塑造一种比较“宽松和谐”的改革空间和政策氛围,让有热情、有魄力、有干劲的领导干部和群众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正向激励”,要给改革者一个“党和人民不会让改革者吃亏受委屈”的明确信号,而且“允许改革者犯错误”并有充分的冗余试错空间,可以在广阔的空间内“大胆地创、大胆地试”,还能够“改革好者有好报”,而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不想改、不敢改、不谋改、不善干”缩手缩脚犹豫观望甚至“为官不为者”,也要给出相应的惩戒和鞭笞。为此,在实操层面及评价机制上,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一定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切实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而又善改能革的干部和群众。
其三,直面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把彻底转换政府角色职能、大刀阔斧削减行政垄断权力作为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攸关改革最终成败的重中之重。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改革,最终共同指向的焦点矛盾和问题都在官僚主义体制本身;从宏观调控到市场监管、从社会管理到公共服务、从污染治理到环境保护,所有民生民权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角色及职能错位导致的,尤其是改革已经过了“外围突破”的临界点而走向“内部攻坚”的深水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长期“越位”、“错位”、“缺位”,该管的没管、少管、赖管,不该管的管了、管多、管滥了,早已成为天怨人怒的“众矢之的”,这也是最终解开“全面深化体制”这个乱麻纠纷者的“总线头”。为此,需要执政党及领导干部有高风亮节的大局意识、坚定不移的政治觉悟、大义凛然的责任使命感,对于一切假公济私、以权谋私采取“零容忍”态度,高扬“全面依法治国”旗帜,稳准狠惩治官僚腐败行为,让所有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心存惊怵戒备,做到不敢贪、不愿贪,且有贪必诛。如此,才能有望真正取得“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胜利。
来源:《特区实践与理论》,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