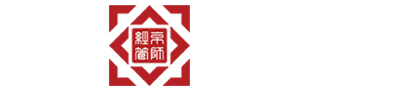不久前,新一轮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正式落地。新一轮改革的一个关键目标便是提高国企活力,而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
但从前期的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这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保持国资控制力的情况下,民资只能作为中小投资者参与国企混改。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因此不少民资对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不高,多持观望态度。
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小投资者的各种权益中,决策和监督权是最根本的权力,其前提是知情权,其结果是收益权,也就是说,决策与监督权处于中心地位。
中小股东缺乏决策与监督权
决策与监督权是法律赋予投资者(包括中小投资者)的法定权力,但与发达资本市场相比,中国中小投资者的决策与监督权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2015年,我们以国际通行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规范,同时考虑中国立法和执法状况,对中国全部上市公司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进行了评估,其中决策与监督权分项指数均值只有35.67分,最大值是75.91分,最小值只有3.19分。从所有制看,国有控股公司决策与监督权分项指数均值为37.14分,最大值为75.91分,最小值为10.45分,非国有控股公司决策与监督权分项指数均值为34.68分,最大值为66.82分,最小值为3.18分。可以看到,最大值出自国有控股公司,最小值出自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中小投资者的决策与监督权分项指数稍好于非国有控股公司,但都处于很低的水平。总体及格率只有0.60%,其中国有控股公司及格率为0.50%,非国有控股公司及格率为0.66%.
无疑,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评价结果,但却是符合实际的评价结果。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的决策与监督权距离国际水平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更反映了中国提升中小投资者决策与监督权的迫切性。
在我国,大股东和经营者对中小投资者施以侵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没有树立起所有投资者平等行使决策与监督权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树立一方面需要法律的支撑,另一方面,需要相应的治理机制的设计。
既然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本质是国资和民资的混合,无疑,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需要高度重视混合中国资和民资的决策与监督权的平等行使问题,而这恰恰是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难点,也是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后来又增加了“抗风险能力”。这句话在现实中产生了不少误解,不少民营企业家据此认为,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因为民资进入既有国企,只能做小股东,最终结果只能是被国资所控制,从而造成民资的决策与监督权得不到保障,这成为民资参与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最大担忧和阻力。一些政府和国企负责人也持同样的认识,认为如果国资不能控制民资,就会导致国资流失,而“国资流失”这顶帽子是任何国企负责人都承担不起的。这成为国资控制民资,进而导致民资进一步失去决策与监督权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对“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不能做绝对的理解。对于竞争性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能过度强调国资对民资的控制,只能强调国资和民资权利(尤其是决策与监督权)行使的平等。可以说,国资和民资混合的关键就是平等,如果过度强调国资的控制力,必然会引起民资的恐惧心理。只有实现权利行使平等,国资和民资才能有效地混合,进而才能形成国资和民资的合力,共抗风险,否则民资非但不愿意进入,而且还会影响企业活力和抗风险能力。
总之,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立足于不同产权主体的行权平等,尤其是决策与监督权行使的平等。不过应当注意,平等不是均等,平等是指按照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规范,企业的各个股东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由于持股比例不同,客观上必然存在决策与监督权的不均等,但只要没有侵害,就不能认为是不平等。
推行累积投票,降低行权成本
目前,一方面,国有大股东“一股独大”,另一方面,政府对国有大股东还有一些政策支持,这无疑加大了国有大股东对中小股东侵害的可能性。因此,政府应该取消对国有股东的政策支持,对中小股东实行累积投票制,这是实现股权制衡,强化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对董事会监督的重要制度保证。很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加之政府支持,使得国有大股东侵害民资中小股东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导致中小股东不仅难以参与决策,也缺少对董事会监督的动力,更难以通过董事会对经营者进行约束,因为他们基本没有可能进入作为决策和监督机构的董事会。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累积投票制是保证中小股东代表进入董事会并参与公司战略决策和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在中国却缺少这样的制度安排。根据我们2015年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评价,在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中,只有20.13%的公司采取累积投票制,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采取累积投票制的公司占20.44%,相对于2012年的12.20%和9.04%,分别提高了7.93和11.4个百分点,尽管进步显著,但仍然很低。基于目前的制度和市场条件,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进入既有国企的民资只可能成为中小股东,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国有大股东享有的政策支持,对中小股东实行强制性累积投票制,便是实现各类股东平等,保证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大幅度降低中小股东行权成本,是保证中小股东平等行使权利的基本前提,也是降低行权上“搭便车”现象的重要方面。降低中小股东行权成本的重要方法是网上股东大会和充分的信息披露,而保证中小股东决策和监督的参与权的方法则很多,如前述的累积投票,以及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上提案、单独计票、网络投票等。然而,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热情却相当低下,这是大股东和中小股东权利不平等的又一表现,也反映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由于参会行权的成本由自己承担,而参会行权的收益则由所有股东共享,加之参会反映自己诉求的可能性很低,于是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时普遍存在搭便车倾向。解决的途径是:除了实行累积投票制调动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监督)的积极性外,还要尽可能降低股东行权成本,可以考虑实行网上股东大会。目前实行网上股东大会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但实行网上股东大会的公司还为数甚少。网上股东大会需要解决信息的完备和真实问题。没有完备的和真实的信息提供,即使实行了网上股东大会,也徒具形式。
根据我们2015年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评价,2014年有中小股东提请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只有10家,仅占0.40%;有中小股东提案的公司只有9家,仅占0.36%;有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的公司有807家,占32.10%。很显然,中小股东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和监督还有很多障碍,这些障碍不解决,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热情是不可能高的,中小股东参与国企混改的后顾之忧也是不可能消除的。不过,这些障碍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上提案、单独计票,还有知情权(信息披露)、维权环境,以及政府的相应立法,如内幕交易处罚法、集体诉讼等。
以相对控股实现股权制衡
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无需追求国有绝对控股。为了避免国有股东一股独大,应尽可能采用国有相对控股的组织形式。即使是相对控股,也要注意避免国有股一股独大。现实中经常有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只要实现了国有相对控股,就不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是否存在一股独大,关键要看在国家为第一大股东的前提下,是否能够实现股权制衡,也就是说,必须有几个民资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国家持股比例比较接近,只有这样的股权结构,控股股东才不大可能独断专行甚至侵害其他股东利益,其他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也会大大增加,而同时也不会影响控股股东对治理的参与,因为其拥有的股权仍然相对较大。政府必须认识到,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不是目的,国有资产增值也不是目的,这些都是手段,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应该是国民福利的最大化,只要国民福利提高了,手段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根据我们2015年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评价,2014年在1008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国有股比例>50%)有297家,占比29.46%;国有强相对控股公司(30%<国有股比例
发挥好董事会的作用
独立董事制度是英美等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通行的制度,独立董事代表所有利益相关者(不仅代表所有股东,还代表其他利益相关者,但股东是首要的)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并对经营者行使监督职责。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通常站到3/2,标准普尔500强公司甚至占到4/5,董事会中只有1-2名执行董事(内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引入中国后,发生了变异,一是被认为只代表中小股东,二是比例大幅缩水,政府要求的最低比例是1/3。之所以被认为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是因为中国有“一股独大”,大股东必然有代表进入董事会,因此不需要由独立董事来代表。由于只代表中小股东,又有大股东独大,占比被压缩就成必然了。
在我国“一股独大”的现实背景下,必须强化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独立决策权和监督权,而要使独立董事有效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必须首先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应该不低于董事会全体成员的一半。根据我们2015年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评价,在1008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比例达到50%的公司只有35家,仅占3.47%;达到1/3但不到一半的公司有964家,占95.64%;不到规定的1/3的公司还有9家,占0.89%。这意味着,中国绝大部分公司只是满足于证监会1/3的最低要求。如此之低的比例,几乎没有否决大股东或经营者涉嫌侵害中小股东的提案的任何可能。
另外,实施中小股东对董事会的满意度调查制度,也是强化中小股东对其代理人监督权的重要措施。在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通常(中小)股东对董事会的支持率应在95%以上,如果不支持率超过20%将视为非正常状态,从而很可能引发董事解体,因为此时董事会已难以代表股东,或者董事会作为股东的代理人已经难以履职。由于这种支持率调查不是以持股比例作为依据的,因此,中小股东可以对不满意的董事说“不”,从而可以更好地反映自己的诉求。这种制度有些类似于西方对国家领导人的“民调”制度。
总之,能否保障中小投资者决策与监督权是国企混改成功的重要因素,政府、企业和中小投资者都应该高度重视,尤其应该通过立法,使中小投资者的决策与监督权能够得到切实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