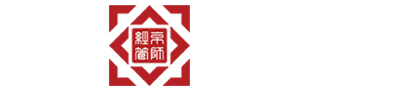教师观点
首页»
教师观点
教师观点
高明华:官商勾结中的公司治理错位
发布时间:2015-07-02
浏览量:
近些年的反腐败暴露出中国政商关系的一个普遍特征,即官商勾结,这种官商勾结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为什么存在如此严重的官商勾结,一个明显的且公认的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且不受法律约束,造成公权可以随意介入和侵害私权,导致创租和寻租盛行,进而导致腐败。显然,杜绝官商勾结和腐败,必须从依法治企,压缩公权入手,而依法治企的实质是强化公司治理。本文只针对竞争性国企进行分析。
政府直接介入公司治理的错位
公司治理是通过建立一套制度安排或制衡机制,以契约方式来解决若干在公司中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安排和利益分配问题。换言之,公司治理是制度范畴,尤其是法律范畴,从这个角度,政府公权力(行政权力)是不能介入公司治理的。但是,政府作为制度尤其是法律的制定者,以及作为国有财产所有者,又是可以介入公司治理的。前者适用于所有企业,政府作为财产保护者而存在,即政府要为企业发展提供规范、秩序和公平,其相应的收益是税收;后者只适用于国有企业,政府作为投资者(国有股东)而存在,它要通过监督(法律监督和经济监督)获取最大化投资收益。显然,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政府的行为都限定在公司治理制度的框架内,而不是以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而介入。
然而,政府介入公司治理的方式却经常错位。现实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政府不是股东,则政府通过设租,让公司治理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如果政府是股东,尤其是大股东的情况下,则政府不仅派出代理人,而且必须让自己的代理人担任董事长,还可以越过董事会直接派人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济师等高管人员。无疑,这是政府行政权力介入公司治理。当然,对于派出的高管人员,可能通过了董事会,但其实通过董事会仅仅是走形式,实质上董事会是被架空的。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中央企业和地方重点国有企业中,政府派出的高管人员很多都具有行政级别,最高行政级别可达副部甚至正部级别。在政府公开招聘的国企高管中,即使没有赋予其行政级别,他们的行政色彩也是客观存在的。从国务院国资委多次全球公开招聘副总经理等高管情况看,由于招聘企业中并非只有国有独资企业,还有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的高管聘用,按照公司法,无疑只能由董事会负责独立选聘,国家作为非单一股东,是无权单独招聘的。在政府直接任命或聘用的情况下,高管出现问题的概率不仅高,而且将无人对此负责。像中石化的陈同海、中石油的蒋洁敏等,由于聘任他们的主体实际上是国资委或上级组织部门,而不是仅仅是走形式的董事会,因此,董事会是不可能对此负责的,而任命他们的国资委或上级组织部门由于是一个个集体组织,也无人对此负责,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不仅国有企业的高管有政府背景,民营企业同样希望有更多的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担任公司高管,这反映了中国企业与政府难以割舍的关系,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聘请有政府背景的人进入企业,是很多民营企业的追求。在2013年度上市公司中,有31.84%的企业曾有政府官员到访(企业对此视为荣耀大力宣传),有12.08%的CEO曾在政府部门任职,有9.77%的CEO为各级人大代表,有6.93%的CEO为各级政协委员。如果统计的对象是董事长,则曾在政府任职、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将会更高。另外,同一企业还经常有多位政府背景的高管。如2009年中国石油的高管中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占比达到66.67%;七匹狼虽然是民营企业,但高管中有政府背景的比例也达到40%。
公司治理行政化是官商勾结的根本原因
公司治理行政化,是对法律的背离。
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班子(执行层)的关系。三者是什么关系?对此各国公司法都有明确的规定,且所有国家的公司法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公司法的规定是: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选聘总经理(CEO)。很显然,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班子相互之间不是一个纵向的等级关系(只有在经理班子领导的生产和经营系统,才是一个纵向的行政管理系统),而是一组授权关系。每一方的权力和责任都受到法规的保护和约束,也就是说各方都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运用空间和对应的责任,任何一方都不能越过边界,违反程序,滥用权力。如果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被“架空”或“虚置”,则会出现股东对董事会,以及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督上的“真空”。
仅就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来说,他们代表的是不同的主体。董事会(包括董事长)作为股东的代理人,代表的是股东利益(现在已演变为以股东为核心的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代表,独立董事作为“中立者”,就是代表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而总经理作为从市场上选聘来的职业经理人,代表的是个人利益,他通过与董事会的契约关系获得授权。董事会是会议体制,董事会成员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董事会中,每个成员是平等的,没有身份高低之分,他们通过契约联系在一起,董事会的决策通过讨价还价而形成,包括董事长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其他人的权力,所不同的只是投票权多少的不同(其实在美英习惯法系发达国家里,由于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绝大部分都是独立董事,这种投票权的差异正在大大缩小),而董事长则不过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并没有高于他人的权力。基于董事会和总经理的这种差异,为了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并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董事长与总经理两个职务应该是分开的。
当然,在公司实际运作中,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分开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取决于公司的规模,以及资本市场(尤其是控制权市场)和职业经理人的发育程度。当公司规模较小时,两职合一可以提高决策效率。当资本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发育成熟时,来自这两个市场的强大的约束力量足以让同时担任董事长职务的总经理实现自我约束。但是,即使两职是合一的,在行使职权时也必须明确当时所处的角色,这样可以保证董事会和经理层两个权力主体的协调和相互制衡。当公司规模较大时,董事长和总经理则必须分开,因为此时二者代表的是更大的群体,二者合一会加大彼此的冲突。当资本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发育不成熟时,由于来自这两个市场的对经理人的约束力量偏弱,同时担任董事长的总经理的权力就会被放大,或者说,总经理侵害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因此,此时两个职务也必须分开。总之,无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位是否分开,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权都要分开,应各负其责。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任的原则是权责明确以及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那么,公司治理是如何演化为行政治理的?这与对公司治理的错误认识有关,也许还存在着故意认知错误。行政治理实际上是沿用政府权力机构的“一把手”观念来治理公司,“一把手”被视作公司治理的核心,而董事长经常被作为“一把手”的不二人选,总经理则是董事长属下的“二把手”,甚至干脆由董事长直接兼任总经理,即使不兼任,总经理的目标也是“升任”董事长。这种“一把手”观念使得规范的公司治理变得扭曲,甚至成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矛盾的根源。本来,独立董事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这种矛盾的。然而,独立董事由于缺乏资本市场的支撑,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做到独立。加之独立董事人数太少,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只满足于证监会的1/3的要求(2013年,全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平均只有36.89%),这更进一步加剧了独立董事的非独立性。加之,董事长这个“一把手”又是政府任命的,因此,公司治理的行政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近些年接连发生的公司腐败(如窝案)以及其中的官商勾结,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董事会(董事长)和经理层(总经理)两个角色混同,以及企业负责人任免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结果,本来的监督和授权关系变成了利益共同体关系。在这些腐败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或者总经理和董事长合二为一,权力过大;或者在董事会中,经理层占据多数席位,而董事长也自认为是职业经理人。在这种情况下,董事长显然就不再是股东的代理人,而是演变为典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经理人。对政府,他们寻求租金;对投资者,他们制造信息不对称,侵害股东利益。尽管国企高管被政府作为“干部”来管理和监督,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和企业资产流失仍普遍存在。
杜绝官商勾结必须强化公司治理
如何减少官商勾结以及由此产生的高管腐败?高管腐败曝光后,人们往往归因于高管的贪婪和无耻。无疑,高管的贪婪是官商勾结和腐败的推动力。但事实上,个体的贪婪不是官商勾结和腐败的根本原因,真正引起官商勾结和腐败的原因是公司治理制度的缺陷,更进一步说,就是公司治理的官僚化或行政化。个体的贪婪只是经济人的本性,在面对丰厚利得时,贪婪永远是理性经济人的最优选择。真正使这些经济人偏离正轨,铤而走险的,是人们对预期非法利得与惩戒风险的权衡,而这种权衡最终取决于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与否。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官商勾结和腐败,最关键的是要完善公司治理制度,首先需要分清何者是治理主体,何者是治理客体。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毫无疑问是治理主体,经理层则是治理客体,二者绝不能混同。其次要提高官商勾结和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加大对官商勾结和腐败的惩罚力度,而这一点又是以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的区分作为前提的。
竞争性国企是市场化企业,其发展方向是混合所有制,因此,对企业负责人的基本监督体制是法律监督和市场监督。法律监督的核心是强化公司治理,实现依法治企;市场监督的核心是健全市场体系,促进自我约束,而市场监督也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
国企负责人可以分为政府董事(外部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高管董事和非董事的高管。他们的来源不同,监督机制应有所不同。由于政府董事、独立董事、高管董事都是董事会成员,因此均应接受股东的监督和市场约束;对于高管董事和非董事的高管,则必须接受董事会的监督和市场约束。
第一,要调动所有股东监督的积极性,以形成监督合力,防止大股东侵害和政府公权力介入。对此,一是实现股东权利平等,国有股东不应享有特权,对中小股东应该实行累积投票制,以保证他们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二是大幅度降低股东行权成本,提高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三是出台集体诉讼和索赔方面的法律,切实保护股东利益。四是实行股东满意度调查制度(类似于民调),如果董事会支持率低于80%,则应启动董事会解体程序。五是在公司控股形态上,尽可能采用国有相对控股,最终股权形态是竞争的结果。六是股东对董事要采取不同监督体制。对于政府董事,由于政府股东是代表公众的,同时考虑到公司经营的独立性,政府董事应设置为外部非执行董事(外部非独立董事),并借鉴公务员监督方式对政府董事进行监督;对于独立董事和高管董事,要通过对这些董事的市场(经理人市场)选择,以及满意度和惩罚等机制来实施强约束。
第二,要强化董事会对经营者的监督,并健全董事自我约束机制。对此,必须把董事会和经营层的职能区分开来,这有利于避免国有股东和政府干预企业经营问题。董事会中必须有较多独立董事,应不少于50%,否则独立董事难以发挥作用。独立董事必须是高度专业化的,而高度专业化的独立董事又来自高度职业化的经理人市场。要根据公司法,实行董事会独立选聘总经理(CEO)机制,并通过董事会备忘录制度使每个董事承担选错总经理的责任。
第三,应在厘清董事会职能的前提下,高度重视企业家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并建立企业家自我约束机制。高管董事和其他高管应来自经理人市场,应明确企业的企业家不应是董事长,而是总经理。董事会(包括董事长)负责监督,但监督不是干预,要充分发挥总经理的能动性,为此必须给予其独立性,包括赋予独立权力和独立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家的自我约束。市场化选择是高能力企业家(总经理)产生的重要机制。高能力企业家有两个要素:一是能力;二是忠诚,这样的企业家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来的,靠政府的“独具慧眼”是选不出来的,也是不合法的。必须建立职业化的经理人市场,市场的惩戒机制能够对现任经理人产生强激励和强约束,从而造就和涌现更多的高能力企业家。市场选聘的总经理不再具有行政级别,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可以做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总经理。要以贡献(企业价值或股东回报)来对企业家进行考核,市场选择和淘汰是重要的考核机制。
第四,要“分层”确定负责人激励方式,以实现国企负责人的自我约束。对于政府董事(外部非独立董事),应实行“公务员基准+贡献+行政级别”的激励机制,薪酬待遇可以略高于同级公务员的薪酬待遇;对于独立董事,应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即车马费加少部分津贴,应通过经理人市场,建立独立董事声誉机制,强调薪酬机制是不利于独立董事的独立的。对于高管董事和非董事的高管,应实行市场化薪酬,但前提是由董事会独立从经理人市场选聘。在经理人市场上,高能力的企业家应有高价格,这是建立企业家自我约束机制的重要方面。
第五,严格信息公开。充分的信息披露对于防止代理人的违规行为(如内部人控制、国资和民资流失、内幕交易等),以及形成企业家的均衡价格,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确保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所有重要事务的信息,包括财务状况、绩效、所有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不能只满足强制性信息披露,更要高度重视自愿性信息披露,这在中国尤为重要,根据笔者在《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报告2014》中提供的数据,中国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于投资者理性投资的需求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量。
总之,要依法治企,实现外部监督与自我约束的有机契合,这是防止官商勾结和腐败的重要制度保障。
来源:《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1期